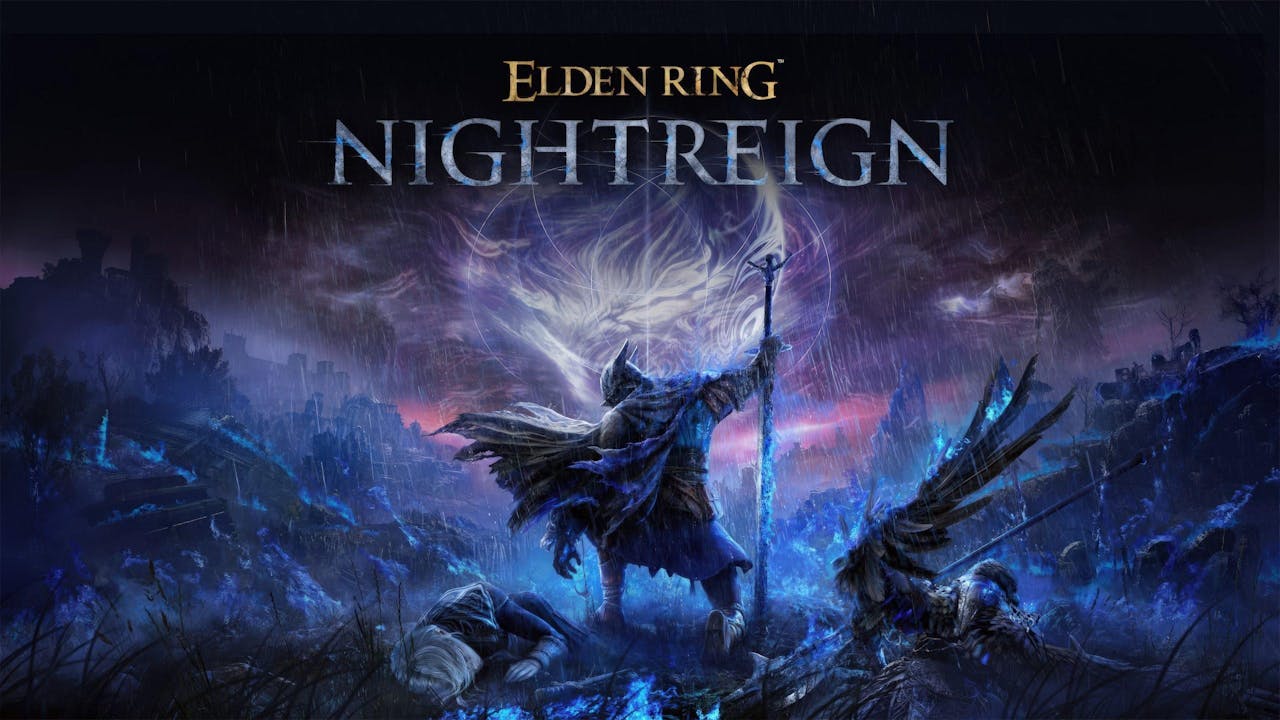理著平頭、雙眼炯炯有神的大直高中公民老師黃益中,先前出了以《思辨》為名的暢銷書,鼓勵社會大眾思考、辯論。隔了兩年,上個月他再度推出新書《向高牆說不》,希望人們培養思辨的能力後,在面對體制所有的不公不義時,都能有說「不」的勇氣。
黃益中在教室外也是台灣居住正義協會的理事長,長期站在街頭為弱勢族群發聲,除了發起「巢運」,也積極聲援同志運動;而去年升格為人夫的他,不僅將彩虹元素帶進婚禮,更邀請了許多同志朋友參加,並在致詞時表示很多人無法像他一樣結婚,希望有情人都能終成眷屬,邀請大家一起支持婚姻平權。
黃益中老師想告訴社會的究竟是什麼?台灣又該如何用教育翻轉一切?透過KNOWING專訪邀你一同進入這位熱血教師的世界,一起談談教育、談談歧視、談談公平正義。
《向高牆說不》同樣也是帶領大家思辨,這本書與《思辨: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》的定位上有什麼不同嗎?
《思辨》的定位是當時我自己投入社會運動時,發現從事社會運動的朋友們都被外界誤解、污名化,覺得那些人好像在製造社會的分裂而對社運份子貼上「暴民」的標籤,所以當時是想把這些從事社會運動的朋友們的故事,寫成教案的一部份,除了在課堂上對學生講以外,也希望傳達給每位老師,讓他們能夠向學生們介紹社會運動的意義,以及他們的人道關懷。
隔了兩年出的這本《向高牆說不》的概念則是當我們啟動了思辯,人們開始進行討論時,就會看到很多不公不義的情形,我稱那些為「高牆」;不管是出現在校園或社會,既然我們已經啟動了思辯的價值,是不是就應該開始一些行動,向高牆說不。像我在書中就有用一句話來解釋,「思辯是一種穿透的力量,這種穿透的力量可以穿越一道又一道的高牆」,譬如像柏林圍牆的倒塌,雖然最後是由民眾推倒,但在前面那麼多年的過程中,都是呈現了民眾嚮往自由的這些價值與精神,所以是思想穿透了這道柏林圍牆,才促成了最後的倒塌。

身在教育現場,學校怎麼建築「教育高牆」?又該如何破除?
這跟校園過去長久以來的價值觀有關,像很多老師都認為校園是一個純潔的環境,社會議題、公共議題都不應該進入校園,所以過去以來他們會用圍牆、高牆將校園與外界隔絕,可是我要問的是,為什麼我們要讓學生受教育?受教育的目的不就是讓學生將來適應社會?
如果我的命題是被認同的,教育就不應該跟社會脫節,過去這套教育價值觀是徹底的錯誤,所以這道高牆一定要打破,但要如何打破,我們就必須讓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社會議題,進行公共的思辨、討論,若不這麼做就會像所謂的「普魯士的教育價值」,以填鴨式的方式教育學生,在學生沒有思考的情況下,只會養出一個又一個複製過的機器。而打破這道高牆,讓學生重新思考,就敢去質疑不公不義的事,這些學生在出了社會以後,才有可能去關心那些被忽略的弱勢族群。
您很重視性別平等這一塊,就您的觀察,台灣教育現場有否落實?
《向高牆說不》中的《歧視高牆》有提到,雖然在2004年開始推動了性別平等教育法,不管是老師跟學生都要上性平課程,但這麼多年以來,我發現這樣的性平教育其實只提到「兩性」平等,一旦碰觸到性別少數族群時,很多老師都會以「有爭議性」、「社會還沒共識」而不教。
其實性別平等教育法先前也叫「兩性平等教育法」,是因為2000年屏東高樹國中葉永鋕事件後才改名為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。我想講的是,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隨不只是兩性平等,重視性別少數族群也是重點。
此外,只要一上到性別少數的議題時,很多家長就會向學校、家長會投訴,要求性平不當教材應該要退出校園,進而干涉老師的教學、打壓教師教書的熱情,成為另一道高牆,這也是我認為最應該打破的高牆。

曾有學生問您關於性別少數的議題嗎?您會如何回應?
曾有個女同學跟我說她是女同志,她爸媽也知道她是女同志,但她爸爸也因此再也不跟她講話,她媽媽則是跟她說「你現在年紀還小,只是不懂事,長大就會恢復正常」,女同學問我怎麼辦,我跟她說,在過去年代裡成長的父母在教育中並沒有學到這一塊,父母沒有接受過這種議題,那個年代的同志也不敢出櫃,因為不了解,所以他們用刻板印象去理解為那是不正常的事。
接著我跟她分享一部名為《滿月酒》的電影,電影講述一個男同志與媽媽的故事,媽媽知道兒子是男同志後覺得很丟臉,在經過一連串的不諒解及衝突後,媽媽終於接受了兒子是同志的事實,最後兒子與同志伴侶透過代理孕母生了孩子,原本無法接受同志兒子的媽媽為他們辦了一場滿月酒,而且邀請所有親朋好友,並向他們說「我兒子是同志,我們過得很幸福。」我用這個故事告訴那個女學生,事情都會好轉,只是沒有那麼快。
對於同志朋友與父母的溝通,老師有什麼建議?
我覺得溝通上千萬不要「硬碰硬」,要相信父母是愛你們的,他們只是不了解。我書中引用了「我支持認識同志教育」粉絲專頁的一句口號「正是因為有所歧視,所以更要認識同志」,我們應該要透過認識教育的方式,讓不認識同志的朋友去理解,同志跟非同志其實是一樣的,大家都是想談戀愛,只是戀愛對象是同性,如此而已。
我也常跟學生提蔡依林的那首歌《不一樣又怎樣》,因為不一樣才是正常啊!過去的教育型態把每個人都教的一模一樣,一旦有人不一樣,大家反而會覺得他很奇怪,若能打破這樣的現象,讓老師把每個同學教成不一樣,這些「不一樣」不就變得很正常了嗎?
所以我建議在跟父母溝通的過程中,可以用「認識」的方式來讓他們了解,用相關書籍、電影讓他們更認識,千萬不要吵架,因為口角上的衝突只會讓衝突的裂痕變得更大。

當性平人士鼓吹同志權利時,會被某些人說是「同性戀霸權」,好像同志才是高牆,您會如何回應他們?
如果反同的團體講的是事實,根本不用怕被別人質疑,但如果講的不是事實,那問題就大了。就像很多家長認為教導同性戀概念,他們的小孩就會變同性戀,那假設我今天教的是英文,他們的小孩就會變英國人嗎?不可能啊!所以你自己的資訊都不對,沒有科學根據、沒有實證的事情,卻一直咬著這個立場,也難怪挺同方會認為反同方是在散佈謠言。
既然沒有實證,反同方反對的原因是?
我認為一群反同方是基於他們特定的宗教信仰,他們覺得同性戀不能存在,但像美國前總統吉米•卡特也曾對美國基督教的「恐同」提出批判,「在耶穌所處的時代,人們歧視痲瘋病,但是耶穌卻選擇與被歧視族群站在一起。而有些基督徒卻無法寬待同性戀者,這些恐同的基督徒,通常具有高度的個人偏見。」
還有一群反對者就是「父權者」,因為在過去的台灣社會中,男性的地位是居高不下的,甚至可以娶好幾個妻子,而這些人從一夫多妻被改到一夫一妻後,男性地位下降、女性地位上升,權力越來越消退,現在連同性戀的地位都上升時,他們就會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戰,我覺得他們反對同志的理由是這樣。
老師覺得同婚釋憲最大的意義是什麼?
同性婚姻其實就是教育的過程,像很多人會覺得現在社會已經給同性戀這麼多權利,生活也跟異性戀沒有不一樣,你們到底爭什麼?既然立專法可以讓你們擁有基本權利,為什麼一定要爭修《民法》?
我用《姊妹》這部電影解釋他們的疑問,《姊妹》是講述一個黑人女傭與白人僱主間的故事,在1960年代,美國對待黑人的方式就是所謂的「隔離但平等」,其中有一段,僱主為黑人女傭在戶外蓋了一間廁所,白人僱主甚至對女傭說「有自己的廁所很棒吧?」但這其實就是「歧視的最高境界」,因為歧視已經內化成了「理所當然」,這種感覺就跟同婚立專法的概念一樣,都已經給了同性戀這麼多權益,我們還要爭什麼?
回到憲法講的人生而平等,我的立場很清楚,如果是人人平等的話,不管你是同性戀、異性戀還是跨性別者,基本上法律上大家所享有的權利每個人都應該擁有,這不是特權,是平權;所以我常說當雙方的立基點不同,對話就會變得困難。

您會如何用同婚釋憲來教育學生?
我們現在並不是說同性婚姻通過後,所有同志都會跑去結婚,因為異性婚姻一直都在,也沒有所有異性戀都跑去結婚;這只是基本法律保障的權利。
而今天大家爭的婚姻平權,其實透過這個運動的過程他們想突顯的是「教育」,讓更多人注意到這件事情,注意到這個國家有多少的同志朋友在社會上、法律上都沒有跟大家享有相等的權利,不應該因為任何原因而與別人有所差別,大家都是一樣的。
除了挺同、反同,您對於不願參與議題、無感的群眾有什麼看法?
只能感動他們吧!畢竟我們不能強迫他支持或反對,有能力的人多做一點,我覺得「感動」可以改變很多事情。
像我書中也有提到,二戰期間時希特勒屠殺了約600萬人,但不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就屠殺這麼多人,這裡面有著很大的結構。我引用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的話來解釋,「起初,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;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猶太人;然後,他們追殺工會成員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;後來,他們追殺天主教徒,我還是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;最後,他們撲向我來,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。」
這就是我常講的「人權的價值」,所以聽了這句話,真的還會覺得事不關己嗎?
您在書中提到了六個高牆,還有沒有其他的高牆是你尚未提到的?
太多了,其實也不用特別分成六個高牆,就是統整出一個概念「威權、保守、單一價值觀」,這道高牆不管在校園還是在社會都是一樣,這樣的概念會限制了學生的多元發展,我們就是要打破這道單一的高牆,讓台灣呈現多元的面貌,最後才能回到平等。
(圖片經黃益中同意使用/來源為黃益中臉書)